今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。1927年4月8日,鲁迅应友人邀请,来到黄埔军校(广州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),为近千名学生作了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演讲……
“革命需要我,我就去”
1927年1月16日,鲁迅离开厦门大学,乘坐“苏州轮”,于18日午后抵达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,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。一时间,广州各家报纸纷纷刊登消息欢迎鲁迅的到来。
彼时,黄埔军校留守政治部主任、中共党员熊雄读了报纸以后,便与政治部的同事孙炳文、刘弄潮商议如何邀请鲁迅到军校演讲。
联想到广州复杂尖锐的斗争形势,熊雄不无忧虑地指出,请鲁迅来演讲,会不会影响他在中大任教和人身安全?刘弄潮分析说,只要鲁迅同意,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:“鲁迅是支持革命的。他赞成办黄埔军校,曾介绍他的学生李秉中报考黄埔三期。请他来演讲,他是不会推辞的。”因刘弄潮1925年春曾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交通员,受李大钊指示多次拜访鲁迅,并有书信往来,所以三人最终决定,由刘弄潮出面邀请鲁迅。
1月25日,刘弄潮来到鲁迅寓所,略事寒暄后,就把话题引到演讲事项上。鲁迅初闻之下略有顾虑,他说:“现在去,怕起不了多大效果。”当时北伐战争还在进行,鲁迅刚到广州,各方势力都在以各种缘由,设法接近并争取、利用鲁迅,如国民党高层戴季陶、孔祥熙、陈公博等先后请他赴宴。但鲁迅不愿受人牵制,一概予以拒绝,因请柬太多,且源源不断,他索性将它们送至传达室,写上“概不赴宴”。
这一阶段,鲁迅除参加校务会议外,或参加欢迎会、或应邀作演讲,忙碌不堪,几无闲暇时间。如3月15日,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写道:“我太忙,每天胡里胡涂的过去……住在校内……从早十点至夜十点,都有人来找。”而在给李小峰的信中(9月3日)亦曾回忆说:“……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,原不过是教书。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……”“访问的,研究的,谈文学的,侦探思想的,要做序,题签的,请演说的,闹得个不亦乐乎。”
刘弄潮解释说:“黄埔同学,尤其是第五期,有许多是过去的大学生,都听过你的课。”他告诉鲁迅,这些学生入学前的文化水平比以往各期学生要高,政治大队的学生大都是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分子,还有很大一批学生是国民革命军一至六军中的有文化的战士,又年轻又有思想。鲁迅听了后终于表示:“革命需要我,我就去,权在革命方面,不在个人方面。”
4月8日,鲁迅在“湖畔派”诗人、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、中共党员应修人等陪同下,来到黄埔军校本部礼堂,作了约两个小时、题为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的演讲。
“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”
演讲一开始,鲁迅开宗明义地指出,在动荡时代,文学的作用并不显著:“这几年,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,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,都渐渐的怀疑起来。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(指‘三一八惨案’)罢,文禁也严厉了,我想:文学文学,是最不中用的,没有力量的人讲的;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,就杀人,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,写几个字,就要被杀;即使幸而不被杀,但天天呐喊,叫苦,鸣不平,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,虐待,杀戮,没有方法对付他们,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?”
随后,鲁迅从“革命时代与文学的关系”和“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”两个方面,旁征博引,深入浅出,分别论述了“为革命起见,要有‘革命人’,‘革命文学’倒无需急急,革命人做出东西来,才是革命文学”;中国目前“没有崭新的进行曲”,“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,正是青黄不接”的时刻,现在到了民众携起手来,为打破一个“旧世界”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了。
鲁迅在此不仅纠正了自己早年片面看重文艺改造作用的唯心史观,而且清醒地认识到,在改造旧社会的过程中,革命的暴力往往比纸上谈兵的文学更为重要,开始强调“武器的批判”作用、“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”。
鲁迅继而又联系社会现实,鞭辟入里地指出:“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,都是旧的,新的很少,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的影响……广州仍然是十年前的广州。”并进一步阐述道:“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,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,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,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。”甚至预言,当革命成功之后,文学中将会出现对旧制度的挽歌和对新制度的讴歌。
演讲最后,鲁迅不失幽默地说:“我呢,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,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更好听得多似的。”台下近千名黄埔学生群情激奋,掌声经久不息……
鲁迅在黄埔军校的演讲记录稿,经誊录整理后,发表在当年6月12日出版的军校校刊《黄埔生活》周刊第4期。后来又经鲁迅修改,收入在1928年10月出版的杂文集《而已集》中。
“革命需要我,我就去”
1927年1月16日,鲁迅离开厦门大学,乘坐“苏州轮”,于18日午后抵达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,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。一时间,广州各家报纸纷纷刊登消息欢迎鲁迅的到来。
彼时,黄埔军校留守政治部主任、中共党员熊雄读了报纸以后,便与政治部的同事孙炳文、刘弄潮商议如何邀请鲁迅到军校演讲。
联想到广州复杂尖锐的斗争形势,熊雄不无忧虑地指出,请鲁迅来演讲,会不会影响他在中大任教和人身安全?刘弄潮分析说,只要鲁迅同意,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:“鲁迅是支持革命的。他赞成办黄埔军校,曾介绍他的学生李秉中报考黄埔三期。请他来演讲,他是不会推辞的。”因刘弄潮1925年春曾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交通员,受李大钊指示多次拜访鲁迅,并有书信往来,所以三人最终决定,由刘弄潮出面邀请鲁迅。
1月25日,刘弄潮来到鲁迅寓所,略事寒暄后,就把话题引到演讲事项上。鲁迅初闻之下略有顾虑,他说:“现在去,怕起不了多大效果。”当时北伐战争还在进行,鲁迅刚到广州,各方势力都在以各种缘由,设法接近并争取、利用鲁迅,如国民党高层戴季陶、孔祥熙、陈公博等先后请他赴宴。但鲁迅不愿受人牵制,一概予以拒绝,因请柬太多,且源源不断,他索性将它们送至传达室,写上“概不赴宴”。
这一阶段,鲁迅除参加校务会议外,或参加欢迎会、或应邀作演讲,忙碌不堪,几无闲暇时间。如3月15日,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写道:“我太忙,每天胡里胡涂的过去……住在校内……从早十点至夜十点,都有人来找。”而在给李小峰的信中(9月3日)亦曾回忆说:“……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,原不过是教书。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……”“访问的,研究的,谈文学的,侦探思想的,要做序,题签的,请演说的,闹得个不亦乐乎。”
刘弄潮解释说:“黄埔同学,尤其是第五期,有许多是过去的大学生,都听过你的课。”他告诉鲁迅,这些学生入学前的文化水平比以往各期学生要高,政治大队的学生大都是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分子,还有很大一批学生是国民革命军一至六军中的有文化的战士,又年轻又有思想。鲁迅听了后终于表示:“革命需要我,我就去,权在革命方面,不在个人方面。”
4月8日,鲁迅在“湖畔派”诗人、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、中共党员应修人等陪同下,来到黄埔军校本部礼堂,作了约两个小时、题为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的演讲。
“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”
演讲一开始,鲁迅开宗明义地指出,在动荡时代,文学的作用并不显著:“这几年,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,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,都渐渐的怀疑起来。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(指‘三一八惨案’)罢,文禁也严厉了,我想:文学文学,是最不中用的,没有力量的人讲的;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,就杀人,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,写几个字,就要被杀;即使幸而不被杀,但天天呐喊,叫苦,鸣不平,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,虐待,杀戮,没有方法对付他们,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?”
随后,鲁迅从“革命时代与文学的关系”和“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”两个方面,旁征博引,深入浅出,分别论述了“为革命起见,要有‘革命人’,‘革命文学’倒无需急急,革命人做出东西来,才是革命文学”;中国目前“没有崭新的进行曲”,“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,正是青黄不接”的时刻,现在到了民众携起手来,为打破一个“旧世界”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了。
鲁迅在此不仅纠正了自己早年片面看重文艺改造作用的唯心史观,而且清醒地认识到,在改造旧社会的过程中,革命的暴力往往比纸上谈兵的文学更为重要,开始强调“武器的批判”作用、“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”。
鲁迅继而又联系社会现实,鞭辟入里地指出:“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,都是旧的,新的很少,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的影响……广州仍然是十年前的广州。”并进一步阐述道:“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,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,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,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。”甚至预言,当革命成功之后,文学中将会出现对旧制度的挽歌和对新制度的讴歌。
演讲最后,鲁迅不失幽默地说:“我呢,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,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更好听得多似的。”台下近千名黄埔学生群情激奋,掌声经久不息……
鲁迅在黄埔军校的演讲记录稿,经誊录整理后,发表在当年6月12日出版的军校校刊《黄埔生活》周刊第4期。后来又经鲁迅修改,收入在1928年10月出版的杂文集《而已集》中。
责任编辑:施丹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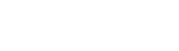


 输入搜索词
输入搜索词







